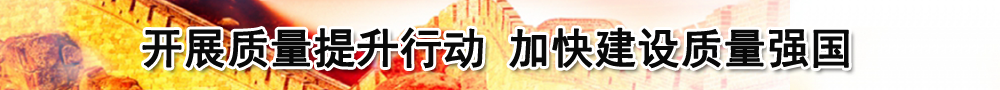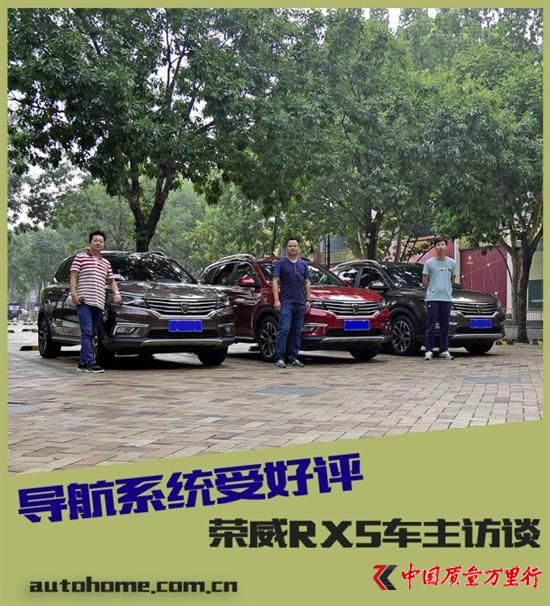從共享單車、共享籃球、共享充電寶、共享雨傘、共享床鋪、共享按摩椅,甚至是共享女朋友……一時間,各種與“共享”有關的概念和項目層出不窮,無論創業者還是資本都發瘋似的開始往里扎,似乎我們真的開始來到了“一切都可以共享”的時代。然而,2015年的那波潮流中,包括“上門洗車”、“上門洗腳”、“上門做飯”等等在內的O2O項目,事后都被證明大都只是創業者和資本們美好的臆想,既難以支撐起一個成熟的商業模式,也很難對于某種恒定的用戶需求提供穩定、可預期的解決方案。

而當下,在整個互聯網業內,“共享經濟”也正面臨著越來越大的爭議,開始被一部分人視為是某種“妖孽”式的看不懂也琢磨不透的存在。
北京驚現“共享女友”
9月14日上午,他趣投放的第一批“共享女友”在北京某商場外的公園里展出。
不過該“共享女友”服務并不是真人,而是共享充氣娃娃。據介紹,目前上線的有五款娃娃,分別是香港、俄羅斯、希臘、韓國和天堂島造型,娃娃還可定制發型、瞳孔顏色、膚色,以及加熱、發聲等智能屬性,也可選購服裝與道具。
他趣方面稱,與一般充氣娃娃不同,共享娃娃由實體硅膠材料制成,與真人的身高體重相同,市場售價為上萬元。在下單后,需支付8000元押金,一天的使用租金為298元,三天為698元,一周則為1298元。支付完成后他趣方面將送貨上門并指導使用方法。使用完畢后,工作人員免費上門回收,押金退回,扣除使用費用。
當然,既然是共享娃娃,不談性,與耍流氓有什么區別。共享娃娃之于用戶的信賴,有兩點很關鍵:安全、私密。如何保證安全衛生?他趣方面稱,首先實體娃娃局部關鍵部位做到每客一換。其次,娃娃回收后將通過五道專業清潔工序徹底消毒殺菌。私密問題方面,他趣作為專業的情趣電商,累積了成熟的成人用品運輸經驗,無論是預定還是體驗過程,都將個人隱私擺在第一位。
共享娃娃的市場有多大?他趣透露的一組數據顯示:重男輕女觀念導致的男女比例失衡將會導致未來中國出現5000萬“剩男”。除了性,他們更需要心靈的陪伴。據他趣負責人介紹,共享娃娃的目標人群,為20-35歲的年輕白領,其中不乏喜愛二次元的宅男群體。另外,也有異地分居的已婚人士。隨著時代的發展,許多人對另一半的期待不再僅限于婚姻,也希望得到陪伴與慰藉。
他趣“共享女友”項目負責人進一步表示,國內情趣市場的用戶群近年來呈現年輕化趨勢,他趣App目前已經擁有5300萬用戶,其中45%以上為90后群體。從他趣社區的后臺數據里來看,男女比例為7:3。作為被智能手機與隨之興起的社交媒體所“支配”的一代,他們的孤獨感正在上升。與此同時,擁有強烈好奇心并且愿意嘗鮮的他們,對于情趣的好奇和接受程度也在不斷增加。孤獨感與對情趣的好奇,催生了共享娃娃的需求。
曇花一現的“共享女友”
共享女友的驚現瞬間引起了一場熱議,不過隨后三里屯派出所以“低俗活動擾亂社會治安”為由對他趣進行罰款處罰,同時要求地推人員寫了檢查和保證書,要求將充氣娃娃帶離北京。
針對這個調查結果,現在他趣終于給出了回應,宣布暫停“共享女友”項目的運營,并下線他趣App內共享娃娃的入口。已經完成預定并交納押金的用戶,將全數退回押金和費用,并賠償雙倍費用作為違約金。
以下為他趣聲明全文:
致歉聲明
我們很遺憾的宣布他趣將暫停“共享女友”項目的運營,并下線他趣App內共享娃娃的入口。
半年前,我們開始籌備“共享女友”項目,本著讓更多人體驗到情趣樂趣的初衷,我們聯合娃娃生產企業,組織專業運營人員,正式立項實體娃娃租賃項目。該項目從建立之初,就以“共享女友 暖心相守”的口號,希望以愛與陪伴為目的,讓價格昂貴的硅膠實體娃娃走進大眾生活。
但在“共享女友”項目上線沒多久,就引起了社會的關注和激烈討論。我們在接到有關部門的通知時,第一時間主動配合了各項調查,并接受了處罰。他趣作為第一家掛牌新三板的情趣電商,十分珍惜App上線五年來運營的小小成就。對于“共享女友”最近給社會帶來的不良影響,特別是重大會議期間的網絡輿論,我們深表歉意,并決定暫停“共享女友”項目。對于已經完成預定并交納押金的用戶,我們將全數退回押金和費用,并賠償雙倍費用作為違約金。
今后,他趣將更加重視企業的社會責任感,但同時我們也將積極探索更加健康和諧的情趣生活方式。
情趣本身并不低俗,讓更多中國人體驗到情趣的快樂,依然將是我們努力的方向。
廈門海豹他趣信息技術股份有限公司
2017年9月18日
隨著共享女友項目的戛然而止,其背后又讓人思考的部分。對此,《新京報》評論員佘宗明則表示,“共享女友”想想都令人反胃,這無關衛道士心態,而是生理性反應。“共享”的梗要被玩壞了。
在以共享單車為代表的分時租賃業務擴充了共享經濟內涵后,“共享”確實成了個“筐”。但靠譜些的共享經濟模式,不只是會抓用戶痛點,還能遵循一條:租賃成本遠低于擁有成本。也只有租比買下更劃算,用戶才會想要“使用權”多過“所有權”。試想,如果騎一次共享單車成本跟買一輛單車差不多,干嘛還要租共享單車?
“共享女友”卻故意逆勢而為:雖然號稱是豪華配置,可在共享汽車都允許“信用分代替押金”的情況下,高昂的押金和租用成本,分明就沒指望有多少用戶。
更何況,在諱言性和講究衛生的現實語境中,就算其標榜衛生有保障,也難改情趣產品消費須絕對隱秘化的事實。這也決定了,有些東西注定不適合“共享”。更別說踩中監管紅線的風險。
這年頭,連“做不了第一個共享單車企業,就做第一個倒下的共享單車企業”都能成為自我營銷的方式; “性+首個吃螃蟹的”,自然也會被“注意力資源即一切”的評判思維奉為絕妙的一著。可低俗就是低俗,即便不秉持衛道士心態,都會覺得“共享女友”是在打擦邊球,“共享女友”想想都令人生理性反胃。就別再毀“共享”兩個字了吧。
共享背后:情感服務開啟商業化
除了他趣線下做的共享女友之外,在微信朋友圈中,“共享女友”和“共享男友”兩款APP的推廣文章被廣泛傳播。文章聲稱這兩款APP上線三天注冊用戶已破百萬,估值百億美元。用戶下載APP后,即可按照自己的喜好選擇不同類型的伴侶,雙方按約定的時間、地點交付“服務”,“服務”結束后可進行雙向評價,公開透明。
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和人們生活、婚戀觀念的逐步開放,共享男/女朋友APP的誕生,正是迎合了一部分人的情感需求。“共享男/女朋友就像過年時流行租男女友回家一樣,已經形成了產業鏈,把個人富余的功能分享出去換得酬勞,這種APP本身不違法,但有些純屬于噱頭。”北京京師律師事務所律師李曉春認為,提供這種情感服務符合年輕一代的情感需求。
“我覺得共享男/女朋友這個想法挺好,千金難買我開心,如果APP上線,我會選擇安裝。”今年20歲的大一女生小微這樣說道,現在在大學生中比較受歡迎的一些校園交友APP并沒有這么多選擇性,“上傳個人信息后,就能靠命運和后臺把兩個人湊在一起,雖然三觀不合但還要完成一周的約定。還有個別交友APP就是風氣不良。”小微認為,共享男/女朋友這樣的APP能“幫我辦很多事,滿足我很多需求,挺好”。
就如小微所說,當下年輕人對交友的需求很多,然而網絡時代所帶來的交友圈的逐漸狹窄,使得年輕人往往無處尋友。也正是人們習慣于通過網絡結識新朋友,人與人之間的親密接觸被網絡聯系所代替,使得“城市孤獨癥”在人們之間蔓延。有學者表示,城市孤獨、極端個人主義和單身人群膨脹將是未來的突出問題。
從這一點來說,北京京師律師事務所律師李江華認為,共享交友APP的誕生是時代的需求。“現在單身男女戀愛、擇偶問題是個大難題,想找個心裡的依托、知己也很難。”在李江華看來,“在當下的網絡時代,隨著人與人之間的親密接觸逐漸減少,就衍生出這樣的共享交友APP,給更多青年男女創造了更便利的條件,預約定制自己喜歡的男/女友類型和相處內容。”同時,在理想情況下,“如果注冊用戶都能具有一定素質和文化水平,租選的男/女友也許會成為普通朋友,也許會成為固定的終身伴侶。在這種情況下既不會有違法律和道德的規范,也能滿足人們情感的需求。”
然而就在前不久,一個名為《喏,這就是你們想要的共享男友》的視頻廣告更是就“共享男友”的定義給出直白解釋。廣告宣稱很多人找男女朋友只是“希望在你需要的時候有人陪伴罷了”,而“想喝牛奶,不一定要養一頭牛。想有人陪伴,不一定要找一個男朋友”。所以“共享男友,應運而生”。
推廣文章傳播幾天來,有人稱這純屬虛構,也有人表示這款軟件已在內測,不日便將面世,有人對此拭目以待,也有人表示對這種有償社交模式不能接受。然而,一些打著“共享交友”噱頭的APP早已上線,隻需注冊,便能在不同性別、長相、價格等條件的人員中付費租賃男/女朋友,選擇接受聊天、約會、吃飯、旅游、充當臨時男/女朋友等相關服務。
花錢可“租”男/女友聊天
好友或伴侶之間聊天時常常會以“聊個10塊錢的”這句玩笑話當作開場白,而如今,聊天真的有了價格。
如今網絡已經有了類似幾款標榜有償共享、有償社交的APP,如“租我嗎”“天天租我”“天天租友”等。這些APP上面的用戶信息包含個人照片、年齡、職業、特長愛好、所在城市、婚戀情況等。注冊后,個人可以隨意提供約飯、陪聊、陪看電影、健身陪同、臨時男/女朋友等多樣而細化的服務,并由用戶個人對自己提供的服務定價,10元/小時的聊天服務在APP上比比皆是,也有陪游、商業陪同等服務價格高達每小時幾百或上千元。
一名22歲的女性用戶在自己的主頁描述上寫道:“每天早安、午安、晚安,陪你聊天,可以叫你起床,可以陪你秀恩愛,可以陪你游戲、看電視、講故事,會撒嬌會賣萌。我只是一個臨時女友,選擇我,就這么簡單。”這樣的服務一天需要50元。而另一名定價為20元/半小時的男性用戶這樣描述自己的服務:“你怕怕,我陪你。你無聊,我陪你,你失戀,我陪你。我一直都在你身邊陪你。藍顏知己是一種在精神上高于老公的愛情形式,讓我成為你的藍顏吧。”
在這些APP上,有的設有身份認證,個人可通過輸入身份證號認證真實信息,但這均屬自愿,并無強制認證。
共享情感服務是否靠譜?
雖然面對共享社交APP很多人躍躍欲試,但還有一些人不禁發出疑問:出租自己的服務或購買他人的服務真的安全嗎?這真的合乎倫理嗎?
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中共黨史系一位副教授認為,作為一種滿足人們情感需求的APP,共享社交APP是一種把個人技能商業化的行為。“如果僅僅是提供聊天、吃飯等服務那么無可厚非,但技能的商業化行為和私密關系的商業化行為存在差異。”
她指出,滿足某個人的戀愛需求這是一種情感勞動,共享男/女朋友的做法不僅將情感需求商品化,其服務內容是否隱晦地暗含“性交易”有待商榷。同時,該類APP用“共享”這樣的語言回避掉了可能存在“賣淫”的實質,“如果兩個人以朋友關系進行親密交往,這種性關系最多屬于‘一夜情’,并不觸犯法律。而這種有償社交模式如果涉及‘性交易’還是違法的。”該教授表示,這意味著人們要正視一點——非強迫性的自愿的“性交易”是否可以被法律和道德允許。
“‘共享’這個詞從字面上看似乎存在一種體貼、關心別人的意味,但在‘共享’概念下,有償社交很有可能是溫情脈脈的面紗下的一種赤裸的、簡單化的、供應給原子化社會個體的交易。”她舉例解釋道:“比如APP‘租我嗎’,名稱看起來似乎強調了消費主義下主體性的概念,聽起來好像挺自由,不像‘賣淫’是被動的購買,這個意義的倫理問題好像被回避掉了。”在她看來,有償社交APP似乎不停地觸碰這種底線——親密關系、情感勞動是否可以交易,用各種漂亮的、符合當下社會人們認同的某些道德語言如“共享”進行裝飾,但“實際上就是赤裸裸的經濟形式,也是一種新的交易形式”。
由此推衍,共享男/女朋友APP無非是“在原子化社會里,用最快捷的方式滿足快餐式情感服務的需求。”這種所謂安全的平臺APP存在虛幻性,“一旦缺失管制一定存在風險。”該教授表示。
“這種有償社交APP在未來并不會成為主流。”中山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柯倩婷認為,“基于感情交流的親密關系是非常重要且難以用金錢衡量的。而共享男/女朋友APP上的這些交易契約不明確,質量難以衡量,容易導致糾紛,難以商品化,且日后交易合法化的可能性很小。”
在她看來,這類APP運營的底線在于,要“基于雙方同意,雙方的意愿得到充分表達,在交易過程中彼此得到尊重,并設有撤回機制,有安全保障。”
其實,不管是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近期公布的新版《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管理規定》,還是此前早已施行的《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》和《即時通信工具公眾信息服務發展管理暫行規定》(微信十條)中都清楚地規定,社交APP注冊用戶應遵守“前臺自愿后臺實名”的原則。“不實名就是違規”,中國政法大學傳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、中國互聯網協會分享經濟工作委員會專家委員朱巍指出,“特別是社交類軟件很容易滋生電信詐騙、人身傷害、介紹賣淫等問題。”
網絡宣傳和網絡內容,除了法律底線,還應該有向上向善、符合社會公序良俗的底線。針對人能不能出租、自己能否就出租自己做決定的探討,“如果只是聊天、吃飯等當然沒問題,這屬于人格自由的范圍,但如果涉嫌衍生范圍的犯罪、違反公序良俗的行為,這種情況性質就發生變化。”朱巍認為,“這不是說法律必須禁止,而是平臺應該具有更高的注意義務和法律義務。”他建議,要監管該類APP,必須實名注冊,通過身份證號注冊而不是僅通過手機號注冊。要主動對實名認證中人的頭像、個人介紹等相關信息進行核查,看是否涉及違法違規內容的存在,審核之后才能上線。除此之外,還要暢通舉報渠道,隨時隨地舉報。一旦出現問題,要按照網絡安全法規定,向公安機關上傳所有相關資料,保存期限不少于60日。